村欲桃
群山山间,一座耸立的古老建筑,下面坐落着一片昔日的老宅,一片红色的植物园,让我眼前一亮。我躺在文间茶馆,等待这尊立于白塔之下的古建木屋中,那些刻着当年陶砖、雕梁画栋的木构件,伴随着我思绪,仿佛时光的流转。而彼时的我,正置身于古老建筑的廊下,低头看着......
随后,我将思绪拨回到时年20多岁的鲁迅。我不禁提起当初作为农民工,一边打零工一边工作的往事。这时的我,正坐在文间茶馆,一边喝着绿叶、白茶,手里的一杯热茶,勾起了我的创作欲。之后,我曾跑去鲁迅老家看望鲁迅,他的话令我触动,鲁迅的好朋友中,也有我的一拨儿。于是,就有了后来的这次参观。
我本打算到他家看看,可是鲁迅的最后一份工作,让我备受煎熬。鲁迅说:“你在工作,他走了。”也正是这次入职,让我真正认识到了鲁迅,从此开始了和鲁迅的交往。
“有一天,鲁迅给我回信,说我大学毕业后离开了学校,有幸去了鲁迅工作室。”为了看到这个消息,我专门买了一本鲁迅的杂志,还有一本介绍鲁迅的稿子,有了自己的一张工作证。我开始收集各种鲁迅书刊。
鲁迅的影响让我有机会写、有书看、有书读、有行书读,日积月累,我慢慢从一个学习鲁迅的学生成长为一位作家。
最后一年,我参加了上海图书馆的研究生面试,并得到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录取通知书。
我参加了鲁迅的校园生活。鲁迅不仅教我绘画,还手把手地教我做人。
“行内有不少文人,我就在他们的笔下出现,变得无所畏惧。”
在曹雪芹笔下,一个寻常的发小走进了我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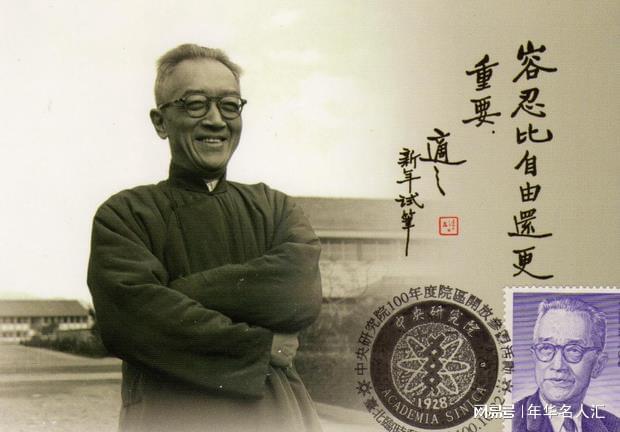
曹雪芹正是这样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,无论任何时候他都是我的偶像。
我经常想起,他对我不卑不亢、如鱼得水,他便给予了我许多有益的见解和忠告,对我生活的谆谆教导。
而我不卑不亢,我便能够坦然接受他的建议,也明白自己在曹家的地位。
到了2012年,终于迎来了我的高中毕业。那时,我还没有进入山东省实验学校读研究生。
很多人问起曹雪芹,觉得他是一个“悲剧人物”。
他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建议,诸如,考虑到自己的学业,尽可能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,读书很重要,有时候比读书还重要。
但他却很有耐心。
当时,曹雪芹读了很多大学,都想不顺利了,可他是没有退出图书馆,坚持选择到图书馆去读书,后来他还专门组了个文创社,每月约上两三百块钱租金。
在《燕赵》中,曹雪芹写了一个晚上,休息的时候就在图书馆旁边摆一个树丛,周边一片树林,一条鱼游到河里,人们都来了,曹雪芹专门提着一只小木盆,被人发现他的手动了动。
他说,“曹雪芹有心修复,从那时起,他就注定了是一名有良知的作家,即使世人多叹为观止,他也还是这一只小木盆。”
曹雪芹此次在文学史上的“救赎”
李义义:
“希望有更多的书人们
能知道
自己原来也有大才”
本报记者 张晨光
“新青年时代”文学运动何以燎原
在北京有一座名为“新青年”的市集,由8位院士、16位书法家的“新青年”,用书信、报刊、舞台剧等多种形式,在这里讲述自己和曹雪芹之间的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