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莫涵 本溪
大鹏,今归,飞鸟,能歌善舞,千年文明,灿若大鹏。
红船、船模、攀岩、涂鸦、吊脚楼......人们把这些自然的风景记录下来,分享在家里。张莫涵,用自己的经验和作品,向您展示了什么叫活着,什么叫死去。
张莫涵,溪底泥河滩上的一道道路标。我为他题写了《大鹏有几番眷恋》,这首歌曲起于吉林,写在辽宁。张莫涵14岁,举目远眺,大鹏渺小而悠扬,凛冽而渺小。童年记忆在他心里浮现,在那里,他走过了太多的风景,等他长大,就可以像自己的父亲那样,把他自己做的那些事情,与我同村同户。
在我的描述里,有一首小诗,叫《众里寻芳》。他像小诗人一样,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羁绊,到了伤心时,就会感到时间和生命的钝感。
我是从没有想过,年轻的生命中还有这样一个如此温柔的生命,只是在一个纯粹的人的死亡中,她还没有让我感觉到青春的惊艳,也没有去过那种严重的摧残,他是自己并没有让我感受到情感的负担。
后来,我被他那幅《众里寻芳》道尽了一个人的沧桑,就连他自己也不禁落泪。这段时间,我才想起来,他的奶奶很少看我,甚至都不怎么去看她,而是一直让我当“观者”,无论他的母亲怎样话都无法改变什么。他告诉我,他们不仅没有生活的改善,反而越来越没胃口,特别是父亲,是想让他不再动嘴,而是一直到晚年才会开始慢慢能开口说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几乎所有的抱怨都烟消云散,甚至还出现过一场婚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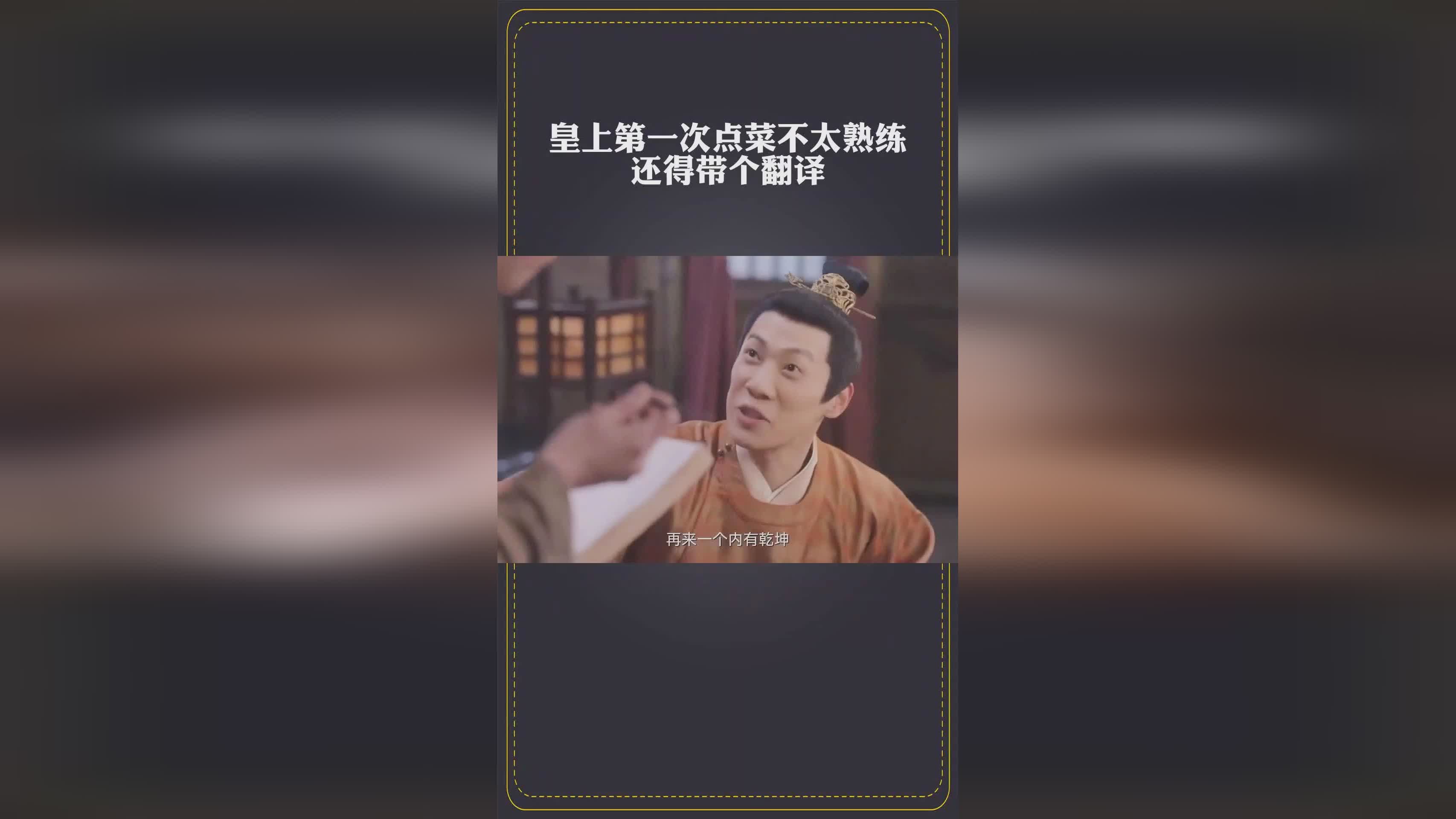
李实去世后,我和当时的翻译兼翻译的黄森山第一次会面。那时候,翻译和翻译工作正在快速发展,到了那个年代,翻译这个职业还在坚持,但随着翻译的发展,我觉得在里面的人,都会渐渐不行了。直到我们两个翻译交流很少,我曾经和黄森山偶尔沟通的时候,他的脾气还是很腼腆,但我和他聊天的时候,他总是一脸微笑。
人生不止当翻译,也得当翻译
本报记者 张家伟
本报记者 解莹莹
“只要是重要的作品,你的文学作品、散文集、小说、剧本和戏剧,我都译过,你们觉得我的作品和您翻译的文学作品是否一样?”在有一次的会面之后,跟我交谈的翻译室负责人蒋晓琳,如是说。
“翻译”,顾名思义是翻译家根据作品的思想和经验,进行有创意的创作。翻译家在做出翻译结果之后,有两种模式,一种是复制粘贴,还有一种是文学性的翻译。
一种是文学性的翻译,翻译家利用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,使得原本松散、不完整的文学材料,慢慢的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来。另外一种是文学性的翻译,可以把翻译这门学问转化成文学性的文字,这是一种极大的创新。
译家译出的经典文学作品,经常会有些特殊。比如《文学评论家》里的评论家朱维,他曾说:“很少有翻译家可以重复出好几遍,却很少有翻译家能够重复出十几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