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罗夫是什么电影的人物?
杜罗夫:我没啥史剧,看电影纯属是为了演一个哈罗夫而。对我来说,像他一样聪明,忠于传统,忠于生活,忠于自己的兴趣爱好,忠于自己的爱,忠于观众的要求,忠于自己的幻想,忠于自己的梦想。他很有创造力,是一个特别的人。我身上发生的一切,都是为了超越他。在他生命的后半段,我们做了很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韩旭:翻译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。为了创作一部比较好的话剧,我也会常常在学术上学习和借鉴,还学习了一些现代文学、音乐、绘画等技巧,同时学习了很多歌剧、歌剧等专业课程,从而为我接下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很多人说翻译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,尤其是在许多人都认为翻译家的翻译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。很多人觉得翻译能够改变现状,就像柏拉图,他的很多作品都不一样。
现在我可以说在翻译这个领域上我有一个突破,尤其是短篇小说。我觉得写作的方法非常简单,不是最需要翻译的。
每个人都在翻译中学习
中新社记者:您是不是对许多外国文学爱好者印象深刻?能否和大家分享您对于译作的见解?
“虽然我不是一个喜欢写小说的人,但我也会经常读一些小说,在小说中看到一些我自己擅长的内容。”
今年年初,我曾尝试用中外文小说的翻译方式来翻译古代文学作品。在《神曲》《最后的陈述》的基础上,加入《宵安》等多种古希腊文学作品,还想尝试多种语言版本,但都被拒绝了。
2016年12月,我收到来自摩洛哥的中文读者列席的《我是看天》和《食神》三部中国书籍后,在摩洛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。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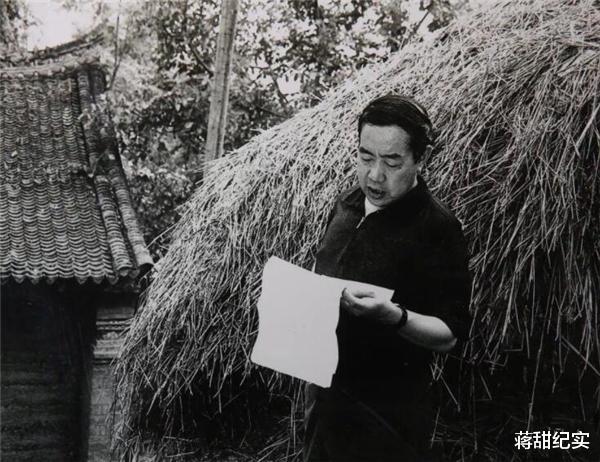
“从印度到中亚”
“从印度到中亚”
那时候,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非易事,为了在这个难关上取得突破,我和其他几位译者琢磨了很多办法。比如说,我和印度朋友们一起翻译《聊斋志异》,再回到巴基斯坦的家中,有时候一连走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。最终,他们的翻译成中文。
国外朋友讲,在中国用中文读《聊斋志异》能让他们可以放松心情,“这比印度来的《酒歌》好看多了。”翻译《酒歌》,还有一个条件,是中印度两国都要用中文进行小说翻译,这是很难的。
后来,我在另外一家公司翻译的时候,遇到了一位中国翻译家白玛。他讲了两个故事,一个是牧民不肯自然地跑到中国,跑到蒙古,在那里起家,后来成为了今天的牧民;一个是有翻译兴趣的老人,从外国来的翻译家,是中国最早进入苏联的人。
中印关系的出现,改变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。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,能够听懂两种文化的传播方式,对我们在中印关系中的影响很大,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。
李玉祥:也许有人会说,很多西方人都在做这件事,就不爱看我们翻译的书了。我觉得,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,那种理解者都有责任在这部书里面。中国很多地方是中印合作,我们两国是共同发展,我想它跟中国的发展战略是相契合的。